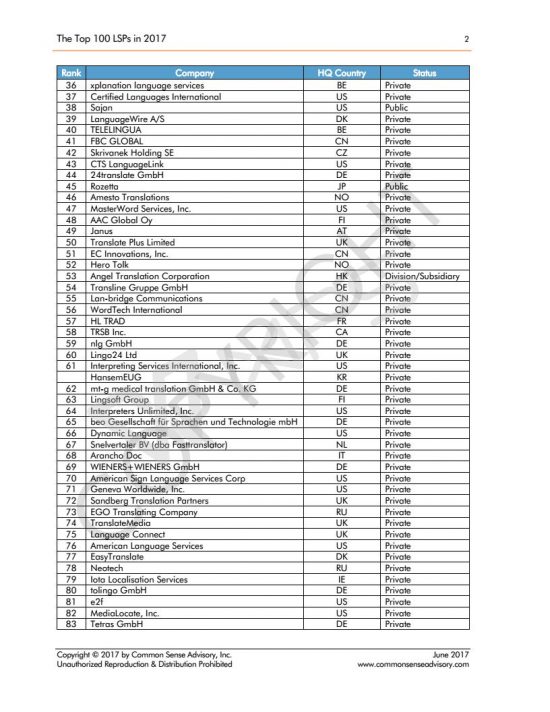外国文学的出版看似争奇斗艳,书架上也是花花绿绿、缭乱人眼,不知者,颇为其所吓倒。其实,据许钧教授指出,今之译文出版市场,旧译本中稍有价值者,几乎无一幸免被剽窃、抄袭或假冒。鼠窃狗偷者有之,公然抄袭者有之,非法盗印者有之。本来属文化积累、借鉴交流之大事,反而弄得邋邋遢遢,硬拼乱凑,浊流横溢,究算甚事!
除去抄袭与假冒,尚有一个不堪的问题,即是所谓重译。《红与黑》新译本竟达8成以上。然而,除了哄取懵懂读者的阿堵物以外,其译文风格、推陈出新是完全谈不上的。有时,我们会很厌烦某些备受推崇的世界名著,原因就出在译本那里。
这就涉及译文的质量问题。老一代译家,若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包天笑、郑振铎、周瘦鹃、周桂笙、伍光建、梁实秋、朱生豪……以及稍后的傅雷、汝龙,他们的译文,或善性欧化或半欧化,或典雅,或浪漫,或稳妥,或轻健,或者把今人早丢到茅厕里的旧文典,如盐化水般浑然无迹地插在译文里用,真实、雅驯之外,其译文尚不时有“撒野”的功力,游刃有余,占尽风流。读者除了叹服以外,更觉得无尽的熨帖、俏皮、激赏。如今看这些旧译本,也就是鲁殿灵光了。说一句无奈的话,自老一代千秋万岁后,恐怕是广陵散绝了!
今日之译本,即便是那些略微像样的,也还是笔下揪扯不清。因为所谓青年翻译家,对外文虽号称精通,不过是长于口语及日用会话,翻译起文学作品来,仍然和词典辗转纠缠;至于其国文水平,更是一知半解,词汇贫乏到蕞尔之微,译文组成句子,简直毫无感觉。人家本来精彩的原文,被他拆得七零八落,通篇给人的印象是在没话找话,扯谈、梦呓;逻辑思想,前后歧出,看到头涨,也还是不得要领。绕来绕去,中文在他的笔下就是不听话。如谓“那些绘画作品即使在它们并没有诱惑我们去进行那种产生众多夭折的怪物的崇高努力时,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于是受了她的牺牲品的欺骗的生活就没管他们而继续跌跌绊绊地往前走了”。(摘自《伍尔芙随笔集》,海天出版社)其夹缠、臃肿、平庸,起伍尔芙于地下问之,她不痛恨中文才怪呢―――假使她以为所有的中文都如此面目可憎的话。而比这丑陋10倍的译文在种种新译本中俯拾即是。新译初起,观者心动,冀盼比梁实秋更梁实秋、比朱生豪更朱生豪的译家出现,今新译已成泛滥之势,却只有出版界有识之士急呼打假!
近代名宿汪康年的朋友陈寿彭给他写信谈译本:“中国文理果佳者,弟愿为之总校。亦不患其所译之附会荒谬,非然者,虽译出为中国字,其文理与西方相去无几,校无可校,改之与重译同。岂不更多一赘疣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030页)他们那一代智识者,特别注重区分中国文理的佳胜与窳败。若下笔佶屈聱牙,或茫然无理,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皆为其所深恶而不取。可以说,重译就是比文笔灵气,因为原著不变,思想、内容已成事实摆在那里,无须词费。19世界中叶,上海墨海书馆的传教士尝拟庞大计划,誓将圣经新旧约全书译为平实流畅的中文,虽然他们的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但事行未几,即感捉襟见肘,不得已,求助于名作家王韬,欲借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王韬看了他们“拘文牵义”的中文,说是“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韬园尺牍》卷二)恐怕只有美化的文行,才能真正把深异的思想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
没有翻译的经验,不知母语之可贵。而新译家率尔操觚,却全不知珍重母语。实则语言洵为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译者的文化积累越丰厚,其笔下文字也就更耐咀嚼。今人之语言在前人基础上形成,可谓无一字无来历,靠字典词典帮忙,拿口水话来糊弄读者,那只能是永远站在文学情境之外的门外汉。
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