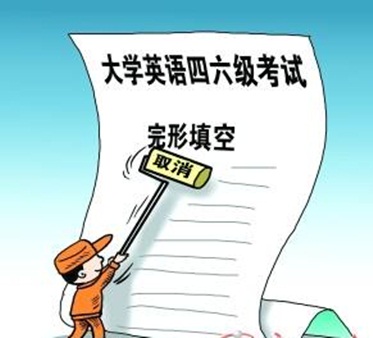梁实秋翻译成就非凡,他用了三十七年的时间独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十几种作品,如《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西塞罗文录》、《织工马南传》等西方文学名著。梁实秋又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强调文学应当描写永恒的人性,强调理性的节制,写有大量的文学批评的文字,如《偏见集》、《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等。梁实秋曾在美国师从白璧德先生,他的文艺思想深受白氏影响。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里,体现在他和鲁迅进行的那场有名的论战中,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中,尤其是体现在他翻译选材上。本文将主要讨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他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
首先我们来看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侯健说,「用最简单的话说来,梁实秋认为文学的内容是基本的普遍的人性,文学要求纪律,亦即理性的节制。」(侯健,1974:155)这一「文学的内容」则深受白璧德的影响。
梁实秋早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作品「至为爱好」,「以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梁实秋,1977a:3)。他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学,先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发表了《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卢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卢骚是法国大革命的前驱,也是全欧浪漫运动的始祖。卢骚的使命乃是解脱人类精神上的桎梏,使个人有自由发展之自由;浪漫主义只是这种精神表现在文学里罢了。」(梁实秋,1926a:110)但自从他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浪漫主义思想进行检讨,写了《王尔德及其浪漫主义》一文,并得到白璧德的赞赏。侯健认为,《论中国新诗》与《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代表着梁实秋思想转变前后的不同观点。前者刊登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的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写作地点为哈佛大学,日期应早于梁实秋接受白璧德思想之;后者写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此时,梁实秋已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在《论中国新诗》里,他推崇感情,宣扬新奇,对郭沫若诗歌大加赞赏(Liang, 1925:55);而《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则是「梁实秋否定自己的过去,转到白璧德大旗之下的宣言。自此以后,他的文学思想与信仰都是它的延续与阐释。」(侯健,1974:150-151)
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是对梁实秋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本书(参见梁实秋,1985)。白璧德的「英国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一课使得梁实秋深为折服。他刚开始时感到白璧德的思想与他的见解「背道而驰」,但读过他的书,上过他的课之后,
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之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主义》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1985:124)
白璧德渊博的学识、精深的思想体系使抱着一种挑战者的心态去上他的课的梁实秋心折首肯,使其文艺思想产生了决定性转变。梁实秋说,「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梁实秋, 1977a:3)从此,他的思想再也没有大的变化。他在《重印「浪漫的与古典的」序》里说,「我对于文学的看法数十年来大致没有改变,也许这正是我的不长进处。我一直不同情浪漫趋势,我以为伤感的浪漫主义与自然的浪漫主义都是不健全的。」(梁实秋,1965a:1)他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梁实秋论文学」序》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从一九二四年到现在,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梁实秋,1989a:13)罗钢在《梁实秋与美国新人文主义》一文作出这样的评论,
如果就理论的直接来源看,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无疑是彻底的西化的,他的几乎每一个基本的文学观念都是来自白璧德或其它西方古典主义文艺批评家。他的一些文章从标题到内容,以至文中的引语、修辞等等都抄自白璧德的著作。(如《与自然风化》等文)。这种抄袭和全盘搬用,即便在学习西方文化蔚然成风的「五四」时期也是极为罕见的。(罗钢,1991:634)
这里的有些说法或许还值得商榷,但至少可以看出白璧德对梁实秋影响之深。
梁实秋是如何来认识白璧德的思想的呢?他说,
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与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新人文主义。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的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他重视的不是élan v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作力」),而是élan 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梁实秋,1985:125)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璧德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中庸」及「克己复礼」的思想有一定的渊源。文中谈到的「健康与尊严的态度」,其实也是「新月的态度」。《新月》的创刊号〈「新月」的态度〉一文也提出了《新月》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与白璧德的思想有吻合之处。这篇文章由徐志摩执笔,但应该是代表整个《新月》一群人的观点。梁实秋说,「创刊之初,照例要有一篇发刊词,我们几经商讨,你一言我一语的各据己见,最后也归纳出若干信条,由志摩执笔,事后传观经过,这便是揭橥『健康与尊严』那篇文章的由来。」(梁实秋,1989b:126)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这里应该有白璧德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极可能是梁实秋施加的,因为在《新月》一群人中,只有梁实秋为「白璧德的门徒」。
白璧德是一个以「人性」论为中心的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说,「他[白璧德]的主张可以一言一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梁实秋,1989a:7)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白璧德认为,为了将资本主义从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拯救出来,就必须向历史以及传统寻找救世良方。他认为,人性存在着善恶、情理的二元对立,只有用理性来进行内在的控制,以克制欲望与冲动,人才能完善,社会才可以走向秩序。
白璧德的人文思想在当时的美国被很多人视为「反动的守旧的迂阔的」(梁实秋,1977a:1),并没有引起大的影响。白璧德在他的著作里不断对卢梭进行批评,因为白璧德极力反对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则要追溯到卢梭,这是他「大处着眼擒贼擒王的手段」(梁实秋,1977a:1)。上文谈到了梁实秋在未接受白璧德思想之前,曾对卢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后来他也着文(比如〈文人无行〉)对卢梭进行批评。梁实秋也极力反对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倾向,他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梁实秋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他主张情感表现应该做到质的纯正和量的有度,文艺应该有严肃性,提倡重理性、守纪律、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典艺术。他在中国的命运也有点类似白璧德,他极力宣传的人性论在当时的中国也受到严厉的批评。鲁迅曾对梁实秋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同时也在他的文章里对白璧德加以讥讽。(梁实秋,1977a:4)美国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拜金主义》(Mammonart)里对白璧德进行攻击,该书后来由郁达夫和冯乃超翻译出版,其翻译的动机以及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看来,梁实秋与他的老师都是鲁迅等人批评的对象,这有力地说明了梁实秋与白璧德的思想一脉相承。在阵阵批判声中,梁实秋奋起还击。在三十年代初次出版的《偏见集》就收录了他的一些文学批评文字。三十年后重印《偏见集》时,梁实秋说,「现在想来,指责我的已不能指责,称许我的已不能称许,我则依然故我,『好执偏见,不通物情』。」(梁实秋,1969a:2)从中可见他立场与信念的坚定。
在文艺思想上,白璧德极力主张西洋文学中正统的古典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以至于法国的布洼娄和英国的约翰孙」,都是他所欣赏的,而由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则是歧途。(梁实秋,1977a: 7)梁实秋也对古典文学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古典文学并没有时间的限制,「顶好的文学就叫作古典文学……古典的就是好的,经过时间淘汰而证明是好的。」(梁实秋,1969b:179)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才是「顶好的文学」呢?梁实秋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梁实秋,1969b:182)但对于什么是人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梁实秋也承认人性是难以界定清楚的,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复杂的,(谁又能说清人性所包含的是几样成分?)」(梁实秋,1928a:23)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说,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理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梁实秋,1929:5)
在这里,梁实秋所说的「人性」有生理的层面(如生老病死、爱的要求等),也有社会的层面(如伦理的观念)。梁实秋还在这里点明了人性与阶级性的轻重之别,文学更重要的是要反映人性。
在政治方面,白璧德的思想属于「稳重一派」,「他赞成民主政治,但他更注意的是『领袖的品质』……他不信赖群众统治mob rule,他的倾向偏向于『知识的贵族主义』」。(梁实秋,1977a:7)梁实秋的政治主张与白璧德也是相似的。在接受丘彦明访问时,他说,
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丘彦明,1988:41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实秋在政治上也像白璧德一样持一种稳健的态度。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受到了白璧德的很大影响,使梁实秋从浪漫主义的立场转到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来。有的学者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建立在二元人性论基础上的理性与理性制裁,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移植和变种,其实质是在新旗帜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背景的具有保守性质的改良主义。」(白春超, 1991:79)而白璧德的影响其实不仅仅体现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上,还反映在他的翻译上。下来,我们看梁实秋的源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
二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其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在选材上面。梁实秋强调文学要有纪律,要有理性的节制,他翻译的选材也同样是由理性指导的。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说,
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最显着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的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仿真。(梁实秋,1997c:11)
梁实秋在这里对于没有理性、没有鉴别地翻译外国作品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非常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反对将西方三、四流的作品翻译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可见他翻译的选材上是十分慎重的。什么是一流的作品,什么是三、四流的作品呢?他衡量的标准与他的文艺思想是紧密相关的,选择的标准就是作品应该是经典的著作,要反映永久的人性。
梁实秋在翻译上最瞩目的成就就是历时三十几个春秋(一九三○至一九六七年)独自翻译完的《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顶好的」,是完全符合梁实秋的选材标准的。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永恒的人性。他多次着文谈论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认识,认为,莎翁全集是「一部超越时代与空间的伟大著作,渊博精深,洋溢着人性的呼吸。」(见胡有瑞,1988:350)「莎士比亚之永久性是来自他的对于人性的忠实的描写。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梁实秋,1966a:2)他还说,
他[莎士比亚]不宣传任何主张,他不参加党派,他不涉及宗教斗争,他不斤斤计较劝善惩恶的效果,戏就是戏,戏只是戏。可是这样的创作的态度正好成就了他的伟大,他把全副精神用到了人性描写上面。我们并不苛责莎士比亚之没有克尽「反映时代」的使命。我们如果想要体认莎士比亚时代的背景,何不去读历史等类的书籍?文学的价值不在反映时代精神,而在表现永恒的人性。(莎士比亚,1966a:3)
梁实秋反复强调了莎士比亚作品对永恒的人性的描写,这正是其文学思想的体现。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
梁实秋在一九五九年青年文史年会(台湾)上的演说中也引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话来谈论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他说,「大家记得在〈哈姆雷特〉里说得很清楚:『戏是时代的、人性的一种表现。』」(梁实秋,1977b:177),他还说,「莎氏在他的戏〈哈姆雷特〉里首先说:『戏剧是一个时代的摘要(Abstract),是时代辗转的历史。』莎氏更有一句名言,他说:『演戏最大的目的是要拿一面镜子照一照人心和人性(to hold the mirror up to nature)。』戏剧不仅表演现实生活,更深一层的表现出人性。」(梁实秋,1977b:184)梁实秋在这里将\”nature\”一词翻译为的「人心和人性」。梁实秋曾多次强调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他在《莎士比亚论金钱》这一译文的《编者按》里说,「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他的艺术是用一面镜子来反映自然。」(梁实秋,1997f:631)他在《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再次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这句话,并作了解释,「所谓『对自然竖起一面镜子』,这『自然』乃是『人性』之谓。」(梁实秋,1966a:2)梁实秋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是如何来处理\”nature\”这个词的翻译的呢?这里的 \”to hold the mirror up to nature\”原文 为:
Be not too tame neither, but let your own discretion be your tutor. Suit the action to the word, the word to the action; with this special observance, that you o\’erstep not the modesty of nature. For anything so overdone is from the purpose of playing, whose end, both at the first and now, was and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 (Hamlet, Scene II, Act III,)
我们先看看朱生豪的译文:
可是太平淡了也不对,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把动作和言语互相配合起来;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你不能越过自然的常道;因为任何过分的表现都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朱生豪,1978:68)
梁实秋的译文为:
可也别太松懈,自己要揣摸轻重;动作对于语言,语言对于动作,都要恰到好处;要特别留神这一点:不可超越人性的中和之道;因为做得太过火便失了演戏的本旨,自古至今,演戏的目的不过是好象把一面镜子举起来照人性;使得美德显示她的本相,丑态露出她的原形,时代的形形色色一齐呈现在我们眼前。(梁实秋, 1974:99)
朱生豪将两个\”nature\”都翻译成了「自然」,而梁实秋将其都翻译为「人性」,并在第二个\ “nature\”后面加上了这样的注释:「原文\”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其意乃谓演员之表演宜适合于人性之自然,不可火气太重。今人往往借用此语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脚注,实误。」(梁实秋, 1974:134)在注释里,梁实秋还指出了将\”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理解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是不正确的。梁实秋还将\”modesty of nature\” 翻译为「人性的中和之道」,其中的「中和之道」很容易使人想到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而这些都是与梁实秋的源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
关于人性论,梁实秋与左翼作家有着不同的立场,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在这些争论中,常常将莎士比亚联系起来。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里说:
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位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特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所以文学作品的伟大,无论其属于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土,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梁实秋,1997a:133-134)
鲁迅对此的反应是,「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鲁迅,1997:136)梁实秋与鲁迅等人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分歧上面。梁实秋在《文学与阶级性》一文里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为例,指出,「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从而得出「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梁实秋,1997e:453)
他在《文学遗产》里的开头就说,
有些自称为左翼作家的人们说:与其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不如读辛克莱的屠场;与其读米尔顿的失乐园,还不如读绥拉菲维支的铁流……理由很简单,莎士比亚与米尔顿是布尔乔亚的代言人,而辛克莱与绥拉菲维支是普罗列塔利亚代言人。普罗文学是革命的,布尔乔亚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梁实秋,1997d:450)
梁实秋反对将莎士比亚看作是「布尔乔亚的代言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认识与争论同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关系。
梁实秋其实也翻译过马克思的作品,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有针对性的,他是用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赞赏来驳斥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文学家的观点。梁实秋选取翻译的文字是《莎士比亚论金钱》。翻译完这篇文字之后,他在译文的末尾加上了《编者按》,
马克思这一段文章很有意义,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天才,其伟大处之一即是他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阶级,他的作品包括所有的人类,自帝王贵族至平民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位置……有人说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说这话的人应该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再看看上面马克思的这段文章。(二)莎士比亚不是一党一派的思想家,他的艺术是用一面镜子来反映自然……(梁实秋,1997f:631)
鲁迅对此也做出了言辞激烈的响应,接连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四日在《中华日报.动向》发表了《「莎士比亚」》、《又是「莎士比亚」》等文迎战。梁实秋在三十年后还说,「说句笑话,连马克思读到〈亚典的泰蒙〉里那一大段论金钱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成篇大段的加以引述,马克思的徒子徒孙还有什么话说!」(梁实秋,1966: 4-5)梁实秋不同意左翼作家所说的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说法,他不仅要为莎士比亚辩护,而且还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翻译出来。而这一翻译活动是他文艺思想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不是迎战武器。
三
梁实秋对《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的翻译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体现,是他对当时泛滥的浪漫主义的抨击。他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情诗创作进行了批评。他说:
近年来情诗的创作在量上简直不可计算。没有一种报纸或杂志不有情诗。情诗的产生本是不期然而然的,到了后来成为习惯,成为不可少的点缀品。情诗成为时髦,这是事实,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呢?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着外来的影响而发生所谓的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的理性也扑倒了。这不